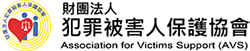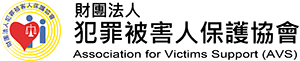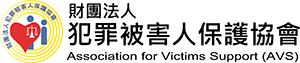馨生之語
把思念化作雲彩

~~~
文燦出事的那個路口離家那麼近,
所以文安都會轉個方向或繞路而行,
他彷彿是怕文燦的身體再度受到傷害。
他的情緒很複雜,心情也格外沉重。
每次經過總是靜默不語,有時驀然抬頭,
哥哥在豔陽下滴著汗珠蹲在開心農場除草的樣子總會出現。
~~~
文安走到哥哥文燦的房間,看著空無一人的小房間和他在這世上留下少少的東西,他在房內來回地走動,心想著和哥哥生活的這些年,有苦有樂,有歡笑有悲傷,但如今什麼都沒有了,哥哥連走都不願意拖累家人,文安哽咽著,強忍吞下淚水,心中感到心痛無奈。就在哥哥文燦發生車禍的那個夜晚,文安揮不去哀慟複雜思緒,反覆深陷在自責的情緒裡。
「早知道當天帶著文燦去婚禮現場就好了,那就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了,如果當天多交代一下友人在旁代為照料或許悲劇也不會發生了。」好多的早知道,但是不管怎麼後悔也已於事無補。最親的哥哥被召回天上去,不可能再出現眼前,即使文安殷切期待著能再看到他憨直的笑容,和哥哥每天胡亂的比手畫腳,看哥哥在烈日下揮灑著汗水跟他招手的模樣,哥哥雖然是殘障人士,或許世俗會投以異樣眼光,但卻活得坦蕩蕩,且勤奮。
哥哥文燦是瘖啞人士,對別人來說可能就是身為弟弟的文安願意照顧傷殘的哥哥,但是對文安而言卻有另一種意義,哥哥不但是他的家人,也是他門前那片開心農場最好的助手。跟哥哥在一起生活,即使有時溝通不便,有時難免也要抱怨幾句,大家覺得都是文安在照顧文燦,但其實他們是互相依靠,有文燦在就讓文安感到心安。
事發的那一天,文安應同學之邀去廟埕廣場的喜宴會場幫忙,出發前他還把晚餐準備好,叫文燦吃完晚飯後別亂跑等他回家。沒想到文燦晚飯過後,像平日一樣從家中步行前往鄰居家串門子,在返家途中又被喜宴喧嘩聲給吸引,覺得好奇想前去一探究竟。就在過馬路時,發生了車禍,文燦整個人倒臥在血泊中,不治身亡。
鄰居發現車禍事故,立即前往廟埕廣場的喜宴會場通知文安,文安說:「原先考慮到喜宴會場很忙碌,恐無法貼身照顧哥哥,所以才會獨留哥哥一人在家,那一天雖然忙碌,但我內心始終覺得不安。從沒想過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一想起來就禁不住淚水直流。
廣場上喜宴會場的霓虹一閃一閃,但文安的心卻有一股傷痛在急速流動著,千頭萬緒,五味雜陳,為什麼被撞的會是文燦?開車的人為什麼這麼大意?為什麼會在別人辦喜事時發生這樣的悲劇。
出事地點是一段每天出門必經之路,一個打開家門就會看見的路口,而他深愛的哥哥魂魄就在那路口煙消雲滅,哀傷之氣在文安家這方圓數十公尺的範圍盤旋著,久久無法散去。
文安生在澎湖,家中有七個兄弟姐妹,文燦排行老二,自幼瘖啞,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文安的父親是製作墓碑的師傅,所以文燦年輕時跟隨父親打磨石頭。父親過世後,因為兄弟姐妹都前往臺灣本島謀生,所以哥哥文燦約於民國七十年左右入住仁愛之家,不過因為哥哥聽覺及語感天生有缺陷,所以自小到大常被欺負。
就在文安結婚生子之後,決定搬回澎湖,翻修老家古厝,也把哥哥文燦接回來同住。文燦是一個童心很重的人,喜歡熱鬧,愛串門子,和鄰里居民也相處得不錯。他平日就協助文安打理家門口的農場,其餘時間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文燦去世後,這個開心農場就不開心了。文安以前總會拉著哥哥走到家中的時鐘前面比手畫腳,告訴他幾點到了就要做些什麼事,幾點到了就要去田間除草,幾點到了就要去澆水、施肥等等,現場還要示範動作給哥哥看。哥哥雖然動作慢了一點,但都會照時間好好做完,那些哥哥在田裡的影像常常清晰地浮現在文安腦海中,這樣好像就能感受到哥哥的溫度。
文安口中描述的過往的開心農場像是一幅美麗的圖畫,與眼前空蕩零星的農田形成對比。
「以前哥哥對於我交代的事物常會丟三漏四的,讓我好氣又好笑,我總是作勢要出拳打哥哥,其實那是我們兄弟間一種親暱的動作。哥哥的陪伴與扶持,早就是一種再熟悉不過了的習慣。」文安說真的好捨不得他。
「少了文燦一起努力的日子,我對於開心農場漸漸疏於整理,現在比較像是傷心農場啦。我每天看到這片田就會想到哥哥,感覺哥哥以前在田裡很開心,悠遊自在的,我哥就是那種安分認命的個性。」文安帶著感傷卻還是笑笑著說。
雖然事情已經發生了三年,訴訟也告一段落,但是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很多工作人員,文安還是要表達感謝之意,因為他們幫了許多的忙。首先,文安說車禍的訴訟真的會讓人焦躁不安、神經緊繃,甚至抓狂。總是在開車時手機鈴聲反覆的響著,文安不厭其煩的接起電話,都是太太傳來的無奈聲音:「唉,家裡又收到傳票了!怎麼辦?」
文安以前曾任職預拌混凝土及重機械工程車司機,「我每天要開著大車在公路上穿梭或在營建工地工作,每每接獲家人電話通知『又收到傳票了』的訊息,就會緊張兮兮。有時候車趟一多,真的就忙到忘記開庭的時間,或錯過了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時機。因為我們真的不懂那些法律,也不知道要注意哪些事情,好在有協會的人一直打電話提醒,要不然我什麼都會錯過。」文安嘆了好長一口氣,因為他心裡其實很擔心肇事者那個孩子。
「有段時間每個星期都去麻煩協會的人,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他們每次都很熱情的接待、耐心的陪我去法院諮詢、遞狀……。我清楚只要收到傳票或訴訟文件,打通電話給他們,他們就會過來幫我。」文安面露靦腆的說著心中對協會的感謝。
對被害人家屬來說,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陪伴的角色,是一種看得見的力量,無論在案發初期提供家屬有關法律層面的權益告知及訴訟過程中的陪伴與協助,都是讓他們安定的重要環節。但是另一方面,善良的文安又掛心著那個肇事的孩子。肇事者才二十出頭,家庭單純,工作穩定,車子剛買還要付貸款!要工作養家、照顧父親及家中長輩,他還有一段漫長的人生要過,文安也不希望那孩子背負刑事責任。他說那孩子年紀輕輕遇到這種事,可能也不知道如何面對。訴訟過程文安總是先想到那孩子的未來,期望在調解過程可以達成共識,讓事情對那孩子的傷害降到最低。然而,調解的過程並不是太順利,刑事案件起訴後,那孩子被判了六個月的刑期,選擇繳納易科罰金之後,便未支付任何賠償金予被害人家屬。
文安的心軟讓太太好是生氣,在調解會上講了一段讓人聽了鼻酸的話,她認為被害人家屬的傷痛是要被看見與需要被理解的,太太的話帶著憤怒、憂傷、悲嘆、鏗鏘有力,對方的確是不該兩手一攤,當做沒事般敷衍,那樣的態度讓人生氣。聽完太太的那席話,只見那孩子頭壓得低低的、看不到臉上的表情,文安想著他應該心中也是很不好受吧。
幾經調解程序,雙方始終未能達成和解,對方強硬態度讓人難忍,彷彿失去生命這件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文安替哥哥抱不平,總想為哥哥做點什麼,於是想了想提起民事求償,他說再艱難也要陪哥哥把路走完。
文燦出事的那個路口離家那麼近,但文安都會轉個方向或繞路而行,他彷彿是怕文燦的身體再度受到傷害一樣。他的情緒很複雜,心情也格外沉重,每次經過總是沉默不語。有時驀然抬頭,哥哥在豔陽下滴著汗珠蹲在開心農場除草的樣子總會出現腦海中。以前文安總是告訴哥哥:「這塊田地是我們的,要一起開墾,一起除草,然後一起好好照料它,不管晴天雨天心情好或心情不好都還是要愛護它呦,絕對不能偷懶。」文安記得哥哥當時充滿信心地拍手點頭。哥哥肯定的神情,事隔多年,文安再度想起來,那個熟悉的感覺依然還在,他的心飄得遠遠的,望向遠邊的雲彩,或許哥哥現在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在上面看著他。